從劇場到影像—林燕卿、許海文、張靜如、蘇品文專訪對談(上)
社交距離的觀影經驗 作品與情感的流動
Q. 去年參與靜觀未來,對策展或其他作品有什麼樣的感受?或與其他影展比較也可以。
品文:那是我第一次在社交距離下看作品,我感受異常地好,現場觀眾的感受好像都異常地好。有種:對,我就是要看藝術!它讓我重新思考,到底我的觀眾應該怎樣去觀賞一個作品,才是最恰當的方式。另外這個影像展也帶給我一個機會,不得不面對,去看我的作品,也就是涉及裸體的部分。以前我拍影片但我從來不看。當我必須要坐在那裡看我的身體作為一個客體展示的時候,我有點嚇到,我就突然之間感覺到,原來觀眾看完《少女須知》的感受是這樣子阿!我覺得社交距離看作品真的是太微妙了,好寶貴。
 |
| 少女須知 影片 : https://vimeo.com/566430533 (攝影:羅慕昕) |
Q. 你覺得那個社交距離的微妙是什麼?
品文:我可以心無旁騖、很獨立的,直接凝視這個作品,我跟藝術家是同一時間存在的,透過這個跟別人的距離和隔開,產生跟這個藝術品更接近的狀態。
伴隨燕卿作品進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那時候我有跟燕卿提議一些在劇場播放影像的實驗可能性,比如說觀眾可不可以躺在地板上等等。可是我們進場後發現是辦不到的,太龐大了。這幾年台灣的舞蹈一直在追求community(社群),參與式、移動式、沈浸式、互動式......各式各樣的,一直想要讓表演者和觀者之間平權化的一個過程;但反而好像在一個舞蹈影像展的過程中,「直接凝視」也促成這次很特別的經驗,而且我覺得蠻成功。
另一個好處是,我因為工作可以看這些作品很多次,像是書毅的《留給未來的殘影》,我發現當我重新再看一模一樣的作品,而導致這個作品產生變化的是我個人的變化時,我發現自己的成長,我還是喜歡這個過程。但是可能展演比較難帶來這個,現場展演很容易因為導演、編導、編舞的想法改變,就很快做出排練場改變、舞作上的變化,所以很難看到一模一樣的東西,表演本來也不追求看一模一樣的東西。所以是兩個不同的認識自己的過程。海文的作品我也看了兩次啊,我好享受我在不同的地方,甚至跟不同城市的人觀賞這些作品時,所營造出來完全不同的生命力,太難得了可以有這樣的經驗。
 |
| 靜觀未來-身體影像短片展 觀影現場畫面 (攝影:呂威聯) |
海文:我的作品《孿生》是一部實驗紀錄片,真實治療過程中擷取下來的片段,曾經在歐洲和台灣一些影展放映,而在「靜觀未來」放映的時候感到最忐忑。由於大部分都是舞蹈領域的人去看,不知道這樣的自己對身體的解釋和態度,台灣的舞蹈人會如何感受,以及觀眾群中也有不少有點熟悉又很久沒有更新彼此狀況的朋友,馬上以這樣裸露的狀態再次會面,感到有點緊張。
 |
| 許海文作品 <孿生> 劇照 |
在靜觀未來中,中國的兩個藝術家二高跟文惠的作品,我感受特別深刻。文惠的作品比較紀錄式,我感受到奶奶和環境的樸實、文惠和奶奶之間的肢體互動、簡潔的鏡頭,導演讓生命個體,環境空間關係還有互動關係,參雜一些旁白和黑畫面文字敘述,這幾個元素之間的融合成非常豐富的內容。二高是肢體造型跟空間的想像力對我來說非常驚艷,畫面很精緻,像一種綺想式的表達。在社交距離的觀看中,我坐在很後面,那個空間感很不一樣,像某種裝置藝術,觀者也是參與者。
 |
| 文惠 影像作品 <和三奶奶共舞> |
 |
| 二高表演 影像作品 <如何辨別黃色舞蹈> |
Q. 海文提到緊張的狀態,那實際在現場跟觀眾互動,有得到什麼反饋嗎?
海文:會有人私底下問我說,那你還好嗎?你現在心情好一點了嗎?身體好一點了嗎?
品文:我覺得很溫馨耶。
海文:每次在影展看自己的影片,最後還是會心情震動一下,會想到觀眾看不到的後面fade out(淡出)一下。製作過程中比較困難的部分,是自己被拍攝,同時又是導演,情緒上的處理是有點困難的。要跳脫當下的情境,冷靜地馬上看回放,注意不只自己的表現還有畫面的細節,再跟團隊討論。內容本身最主要是情感上的表達。有些我很感動的回饋是觀眾描述自己跟他身體的感覺、對身體的想法是什麼,這部分是我想達到的,希望這部影片是給大眾看,能在情感上有些觸動,進而對自己身體有些想法。
靜如:我覺得書毅在第三場有把一些做行為藝術的影片也納入這個範疇是好的,因為對我來講要弄一個身體影像展的話,確實不需要框架什麼是舞蹈,或是本身的提問就是:什麼是舞蹈?這也回到剛剛燕卿說過的,她拍那些風景,那些風景本身就是在舞蹈。所有參展影片都是創作者用他的想法在為心中的舞蹈定義。
書毅會請創作者上台問答,我在問答中的表現被他唸了一整個晚上。他要我介紹我的影片,但我本來就是比較怕生的人,對我來講在不熟悉的場合面對大眾去談我的創作思維,一直不是很習慣也有點排斥。那時候算是第一次以一個影像創作者的角色去回答問題。我覺得我沒辦法很好地用口述去表達這個影片要處理的東西。但那也是我要學習的,不管是劇場表演或影展,我怎樣以一個創作者的角色和觀眾溝通我的作品。
 |
| 圖上左起 : 創作者 - 張靜如 . 周書毅 . 鄭立曜 . 吳承恩 圖下左起 : 散場後的團隊合照 ~ |
Q. 其他三位都有在現場和觀眾分享作品過,我們請沒辦法到現場的燕卿來說說你的作品。
燕卿:剛剛阿怪說的我都懂!如果我沒有辦法用我的文字述說我的作品的話,觀眾可能真的會被我的文字或是我的談話誤導。但如果真的要跟觀眾分享,我覺得是你看到什麼就是什麼。作品中有很多片段可能是每天生活上會遇到的片段,或是殘留在腦海中很久的記憶的片段。這支作品是在疫情中倫敦封城下做出來的,很多安靜的時候,加上我選擇不要有聲音,在沒有聲音的當下去觀看,某些感官可能會因為沒有聲音的刺激而被打開來。因為聲音有時候會很直接地影響到影像會往哪邊走。
 |
| 林燕卿 影像作品<斷> |
我覺得疫情下安靜是一個解放,好不容易在一個大城市裡面終於沒有聲音了!當下不可能完全無聲,身邊所有的聲音就是自然界的聲音,車聲、人聲都很少。做這支影片,看到人類的渺小,每天看到周遭環境是一直在變的,可能是身邊的雜草,或是池畔裡又生了小鳥或天鵝。
影片裡很多大自然出現,因為它是在當時讓我感到最有生命力的東西、蓬勃的,人類反而是最無助的。間接也在支持著被隔離跟封城的人,當自然環境的循環還在運作,人類世界被迫要停止。很多片段是在疫情時讓我可以更把他們連結在一起。
觀眾有選擇權,想要看到什麼就是什麼,對我來講是一個開放的議題。如果你看到環境就看得到,如果你要看到人類的殘忍也看得到,如果你看到漣漪、反射也看得到。
每天可能會走一兩小時的路,看到比較多的是漣漪、反射,跟水比較有關係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吸引到我,能讓我覺得平靜,在這樣的生態下。因為周邊的環境不像疫情前台灣(訪談時台灣還沒開始封城或停工停學),在這兒永遠一直處在隨時工作被取消狀態,這個不確定性變成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anything could happen(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我想問剛剛海文講到私密或難以啟齒,關於身體還是情感還是那個情境?
海文:比較是關於情感的。
燕卿:因為剛剛她讓我想到,我作品中很多碎裂的片段,會連結到個人的情感,要怎麼試圖打開潘朵拉盒子。在疫情裡讓我去翻這些東西時,有點讓我去拿一把鑰持把那個盒子打開,至於打開後有沒有好好把它處理,我還不知道。每個盒子打開的每個片段可能連結到不一樣的情感或生活,有反映到某些我在講的東西。畫面的截取有些很直白,有些會是意象。在創作時時,我把它看成像是一幅一直在移動的畫,不管框架裡的媒材是什麼,是人的身體或大自然或路上的風景,這些媒材都有它要通到的線跟點。連結到我的作品到現場時,比較像是移動的畫。那是我本身看東西的方式。很像實驗室的顯微鏡裡面細胞的轉換。
 |
| 林燕卿 作品 <斷> |
從劇場到影像 / 下一個影像計劃
Q. 想請問各位劇場跟影像媒介創作上的不同?從創作構思、工作過程、參與人員、分享方式與獲得回饋的方式等等,從在腦海裡到實踐都有很多不同,想聽你們談談特別有感觸的部分。
海文:我的影像養成是在一個做當代視覺藝術的環境裡面,透過大量與其他視覺藝術家討論的過程構想《孿生》,重點放在平面當中看到的東西,讓肢體的表達影像化,要怎麼轉化。《孿生》之後我創作了一個錄像裝置,空間裡有兩個屏幕。劇場的觀看視角會影響你的路徑而去改變,所以會更注重在那個路徑上所有的可能性,都要把它想進去。但是在單純影像上面,我會專注在單純在這個平面上面你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我覺得在做影像的過程,差最多的可能是,做劇場的時候不斷排練排練,但就只有表演那次是最重要的,每一次的演出又不太一樣。但是影片就好像有好幾次的小表演出現,最後完成之後,就沒有我的事情了,時間上好像就被凝結了一樣,很永恆的,固定在那邊,不斷被播放。
 |
| 許海文 作品 <孿生> 劇照 |
品文:我覺得這是個好深刻的問題,因為確實關係到時間感不同形式的展現。我們在嘉義「舞蹈.南方」時中場休息有亮燈,我們有紙本的節目單,也因此有一些觸覺的事情幫助他landing(降落),幫助他從觀賞藝術作品時一個浮空的狀態中,透過一個體感經驗,回到日常身體,從零再出發。可是我發現在看舞蹈影像的時候,不是每個作品都能帶我的身體同一時間感覺身體地去觀賞這個時間性,有些東西真的就是視覺主導,我在看的時候會忘記身體的存在。有些反而恰恰相反,我在看的時候,特別感覺我的精神、身體在那個當下跟作品在一起,跳脫出很不同的體感經驗。作為一個喜愛劇場的人,我比較傾向是在觀賞的過程中,我的身體也同一時間存在。我覺得這是我做影像和做劇場之間,最難以調度過去的一個很精確的挑戰。
海文:我在學校的時候,最常被質問的是說,有一個舞蹈段落在影片裡出現好了,那為什麼不直接在劇場裡面看你跳就好了?在這個影像中,舞蹈怎麼被呈現,所謂影像化的過程這樣子。看影片跟劇場的體感經驗,差別是很大的,我覺得影像能夠呈現、承載,或是它的強項,跟在劇場裡面的強項是完全不一樣的。
Q. 嗯,劇場裡的體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個身體的存在、在場。
海文:劇場裡面的體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觀眾可以自由去選擇。但是影像當中,創作者在鏡頭當中所指涉的是更精準的,它多義性的展現是在,可以怎麼樣在你看到的東西之外,啟發更多什麼樣的東西。劇場裡觀者的視線是可以有多樣性、重複性的,整個過程會形成一種動感。
Q. 海文說在學校,是在學校念什麼?
海文:我在法國的生活後期(2017-2019)進入當代視覺實驗室(le
fresnoy - studio national des arts contemporains),是兩年的藝術創作進修,在我之前也有不少台灣藝術家曾在Fresnoy進修,譬如林其蔚、許家維、黃邦銓等等。Fresnoy的特殊之處,並沒有課程,而是邀請不同領域的藝術家陪伴同學的創作過程,同學們大多數以視覺藝術為主,那邊有軟硬體,硬體方面最完整的還是電影方面的攝影器材和後製的軟硬體。等於是在一個電影後製的基礎之下,同學盡情發展任何形式的創作。
Q. 你之前也是舞蹈系畢業的對嗎?
海文:我是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的,畢業後就去法國了,在法國生活初期在法國國家編舞中心進修一年的肢體創作,之後就在不同的舞團跳舞。到了某個時間點我感到想要休息一下,學習其他東西,想要找自己創作的方式。我本來就對影像很有興趣。
Q. 剛剛海文提到觀者視線跟景框也蠻有關係的,這個視線除了你剛剛提到的動感之外,觀者在劇場裡面很能自己創造敘事,這個多焦可以讓觀者創造敘事,選擇自己要看的東西。
海文:劇場畢竟還是有一個時間軸上的敘事,但裝置的話就是觀者從自身的感受中拼湊。
Q. 海文接下來應該會繼續做影像創作?
海文:影像對我來講是接下來創作一個蠻重要的媒介,以及我越來越傾向做完一個作品後時間被凝結,完整度不會被改變,這樣的方式是我比較喜歡的。但不代表我不做表演了,只是影像我一定會繼續做。前幾年有些想法,還沒有實踐出來,現在會想實踐出來。
Q. 可以分享一下近期率先想實踐的嗎?
海文:最近有在緩慢進行一個從八仙塵暴事件得到靈感的計畫。目前我感興趣的比較是身體認同的矛盾性,特別是身體上受過一些創傷,經過創傷後在生活當中有些對身體的不認同感或錯亂、疑惑,是我目前在關注的內容。八仙塵暴主題有一部分是我對溫度及場域的興趣,在一個樂園裡面發生了火災,裡面有火和水的元素,裡面的人受到身體上的創傷後,身體上的感受,以及這些感受帶來的生命上的疑惑。
品文:雁婷剛剛是說劇場作品具備多焦嗎?
Q. 對,我是說劇場。譬如說疫情中有非常多劇場作品被影像記錄下來,在線上播放,我可以想像原本在劇場裡面的狀態,我相信一定是更好,包括裝置、聲音動態、表演者的走向動向,觀眾在劇場裡是有選擇的,我可以決定我要怎麼看,怎麼拼湊起整個畫面和聲音的感受。可是當它變成在電腦螢幕上看到的影像,攝影機已經幫我選擇焦點和視角,我無法選擇。像你們在做影像創作時,視角就是由創作者選擇,要給觀眾看什麼東西,怎麼串連,怎麼轉換視角。
品文:我在台灣的處境是有點過度倚賴電腦和手機螢幕,可是實際上這樣的螢幕並不足以構成當我要做影像創作時的力道。
靜如:我同意品文說的。某程度這也關係到創作者訓練過程。譬如電影創作者也是在電腦上剪輯,可是他必須預期之後是以電影院規模放映,呈現的方式會影響他剪接和畫面上的選擇。畫家也是,如果他要在一個很大的畫布下創作,那個體感也跟平常畫一個小畫布的體感很不一樣。如果要做影像也會把這個東西考慮進去。
品文:我看了非常多東西,我每天都在看影像,可是還是沒有辦法構成我需要的養分。
Q. 品文覺得是為什麼?
品文:我在想是不是跟我的藝術選擇很有關係?我的藝術選擇本來就讓我不容易找到高度共鳴的作品呢?
Q. 妳在看的這些影像有在妳的藝術選擇中去開展、尋找妳想要看的東西嗎?
品文:一直都還是有所選擇,但是有太多東西可以看了。台灣是一個高度影像化的情境,不管是直播主、網紅,各式各樣的,表演藝術一直也都是啊,只有變得越來越多,可是越來越多並不表示有接近被藝術籠罩的過程。我覺得透過影像被藝術籠罩這件事是很龐大的,這個東西會馬上給我很大的動力,但不在日常裡發生。看很多不見得代表它會帶著我的創作更往前。
Q. 那現在要怎麼辦呢?還會繼續做影像嗎?
品文:其實我有在規劃一個計畫,可是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始。我想要做女性主義A片。我今天恰好看到一個集資網站要做給女性看的A片,可是這並不等同於女性主義A片嘛。所以我覺得,伴隨著有些人有更多的資源,我們女性主義A片要怎麼開始第一步有點困難。我目前還在觀察社會的流動去理解,在什麼時間提出這個想法是最佳時機。我們有一個洞,這個洞只有女性主義A片能去填補它,那個洞會在什麼時機發生,我還在觀察。我覺得女性主義A片在我心中是等同於電影製作的規格,涉及一個產業鍊的製作途徑,這個產業的結構長相是什麼,我比較在思考這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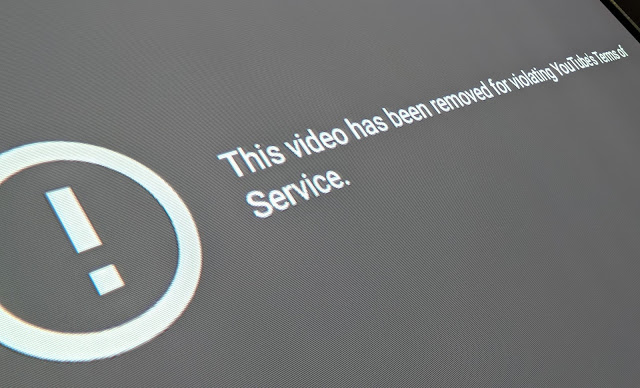 |
| 蘇品文 作品 <異鄉> 影像擷取撤拍畫面 |
Q. 那剛剛談劇場和影像媒介創作的不同這題,大家還有想要補充的嗎?
品文:我在製作劇場的時候是以一個long-take(長鏡頭)的方式在做作品,但是不等同於我可以用同樣方式做影像。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又很擔心在過度的分鏡、剪輯,各式各樣的素材介入,導致最後的影像呈現過度精緻,以至於降低了觀眾可自主觀看、對立的可能性,那個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不同。因為劇場語言絕對是很精確的,劇場比較能夠維護各種角度,影像確實比較難。當影像要維護一個多角度,又要維護長度和密度的時候,那整個技術本身是我目前沒有那麼多心力去處理的。我劇場都快搞不完了。影像對我來說有點太遠了,短短的可能還好。就算我以後要以影像作為媒介,像剛剛提到的女性主義A片,也是會以劇場呈現的方式來呈現,而不是播映一個女性主義A片的完成品。現階段我會比較寧願保留劇場性,但是借用影像來做一個女性主義的討論。
靜如:對我來說,用來再現(representation)的媒材不一樣的時候,整個思考方式就不一樣。去感覺劇場表演的方式,跟去感覺影像作品的路徑不大一樣,當然製作過程也很不一樣。譬如以「靜觀未來」裡面播的《0 1 DO》來講,現實條件促使我要一定要用影片製作流程去工作。首先我的拍攝地在法國,我可以拍攝的時間只有兩個禮拜,很多前置作業要在台灣進行,拍攝完也要帶回台灣後製。所以整個過程要仿照劇組拍片的模式進行才可行,因為要在一定時間內完成。
 |
| 在法國Le Phare編舞中心駐地創作的張靜如作品《0 1 DO》 ( 左起舞者 : Fabio Bergaglio、楊壁嘉、楊雅鈞 ) |
另外,我要找舞者來演繹身體語彙,也要有攝影夥伴來操作攝影機,所以這中間有我跟舞者、攝影師的溝通,還有跟一起剪接的夥伴討論影像的選擇,所有製作時程要安排得很精確。劇場也有時程,可是很多時候是稍微混融的,譬如誰來看排、討論後有新的想法可以在下一次的排練去試,很多機動性和彈性,每一次排練都在生長。可是做這支影片時最大的彈性反而在最後的剪接。但本來以影像呈現的時候,我比較著迷的地方也在影像蒙太奇的部分,影像連接之後可以創造怎樣的敘事空間是我關心的面向。
Q. 靜如之後還有什麼影像的計畫嗎?
靜如:今年有拿到國藝會補助,會把之前在新人新視野做的劇場作品做成影像版本。
Q. 所以接下來很有趣的是,我們會看到你怎麼樣用影像來轉譯當初這個劇場作品。
靜如:當初申請補助也是給我自己一個功課,我也是想要繼續以影像創作。我們在做劇場作品時也會有錄影場,可能架多台攝影機,拍攝出來也會剪接成一個影像版,但我們不會把它當作一個舞蹈影像作品。劇場紀錄跟舞蹈影像作品中間的差異是很有意思的。我先前已經先做了一個劇場作品,也有那個版本的影像,那我現在怎麼打破這個東西,重新用影像為出發點去做這個創作,對我來講是給自己的一個功課,我想會完全不一樣吧。
燕卿:剛剛阿怪提到把劇場版轉換成影像版,在英國因為疫情的關係,所有東西都變成影像在網路上播放,到現在因為沒有辦法演出,我們也會為了劇場版而重新拍一部影片,當然敘事手法就變成導演敘事手法,時間也變短。
靜如:之前跟一個朋友的友人碰面,他說在百老匯,也會因為覺得那個場地空著很浪費,乾脆運用那個劇場空間拍影片,做線上的放映。
燕卿:對我來講劇場跟影像創作本來就兩個完全不同的切入點,這幾拍攝這些影像的時候也在想,有沒有可能從我拍攝的影像裡面重新學習,把它變成現場?最近在想,怎麼把那些拍攝捕捉到的影像,轉換到身體上,讓它很單純用身體去表現出影像裡想說的。重新去學習那個虛跟實。
 |
| 林燕卿 影像作品 <斷> |
我尋找的影像都是在當下發生,沒辦法重複了,所以當我回來剪接的時候,我可以去用到當下的那個瞬間,而不是我刻意去找的。影像沒辨法取代劇場的是它的臨場感,但有些影像就是等待它的臨場感發生,就是剛剛品文提到的體感的體驗。當然我不是專業的,但當我拍攝影像,回來再看到的時候是一個再學習,把這個拍攝過程學習到如何可以用在劇場裡呈現。現在很多劇場結合各式各樣的媒材在裡面,我自己比較有興趣的是,怎麼樣讓影像跟身體在劇場中虛實交疊,相互反思。
靜如:剛剛講到劇場可以用多種角度觀看,我覺得影像在素材的並置或拼接之間,也創造了一些辯證的討論在裡面。我覺得是方向性的不一樣,他們要跟觀眾溝通的路徑不一樣。
Q. 那燕卿有什麼新計畫嗎?
燕卿:還是會繼續探索下去,每次看到有什麼對我有啟發的,有興趣或者是有對話的,就會拍下來,因為不會再重複了。一直在搜集不同的資料、影像。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影片會被選進「靜觀未來」平台,當時只是單純的想,有這些素材為什麼不試試?對我來說是個鼓勵。因為這個平台,讓我覺得自己對影像有某方面的敏感度,可以繼續研究、繼續探索與發展下去。對我來講是還在學習的階段,繼續探索中。
訪問是在今年一月進行的,在文章上線前,和所有與談者最後確認,此時很多狀況都改變了。最大的改變是,當時還在分享倫敦封城經驗的燕卿,現在可以旅行到其他城市做戶外表演了,而台灣進入前所未有的三級警戒。燕卿說:「觀看台灣新聞,加上這邊慢慢解封,所有東西有點一直在不同時空裡,一直和台灣有種平行時空的狀態。」如果現在重新訪談,想說的話也會截然不同。她告訴我要珍惜現在的安靜,過陣子就不會再擁有這種慢與安靜。經歷過封城、解封,現在暫時恢復自由的燕卿,也提醒道,不只是Covid在我們身旁,自然環境的破壞、人類的廝殺、種族歧視、氣候變遷等都還繼續在發生,我們不要被疫情洗腦,自然界一直在跟人類對話,但人類似乎一下子就會忘記。
未知仍未知,但隨著每一次經驗未知,我們的生活方式、面對態度也一直在學習、轉變,回不到從前,我們就在新的日常中找尋出口,建立新的習慣。創作、展演模式也都重新建構中,這篇訪談恰好在轉型混沌的縫隙間,一兩年後再回頭看這些紀錄會發生什麼新的對話嗎?未來會如何呢?我們持續靜觀。
文 / 許雁婷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